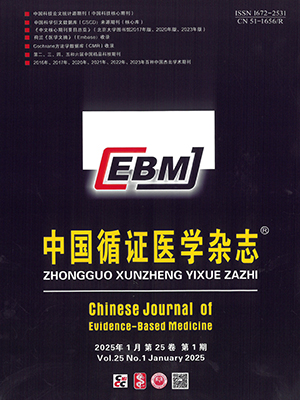引用本文: 方嘉敏, 梁好, 鐘錦濤, 陳木欣, 楊曉敏, 趙怡迪, 魏琳. 認知衰弱與老年人死亡率及住院率相關性的Meta分析.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4, 24(6): 686-692. doi: 10.7507/1672-2531.202310219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中國循證醫學雜志》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老年人的健康問題逐漸成為焦點,其中認知衰弱(cognitive frailty)作為健康老齡化[1]及癡呆癥二級預防的新方向[2],已成為國內外老年醫學研究領域的熱點。認知衰弱作為衰弱的一種亞型,是指個體在排除癡呆的前提下,同時存在軀體衰弱與認知功能障礙的臨床狀態[3],其會增加老年人發生跌倒、殘疾、抑郁等不良結局的風險[4-7]。而死亡和住院作為最常見的不良結局指標,是醫護人員尤為關注的重點,既往有研究表明認知衰弱是死亡及住院的獨立危險因素[8],但也有研究認為認知衰弱不會增加死亡[9]或住院[10,11]的風險。目前認知衰弱與老年人發生死亡或住院是否獨立相關在不同研究間尚存在爭議。基于此,本研究將系統檢索已發表文獻,通過Meta分析探究認知衰弱與老年人死亡率和住院率的關系,旨在明確認知衰弱是否會增加老年人死亡和住院的發生風險,為開展早期篩查老年認知衰弱并及時干預提供可靠的依據,以提高老年人的軀體功能和認知水平,最終實現健康老齡化。本研究已在PROSPERO注冊,注冊號為:CRD42023430153。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隊列研究。
1.1.2 研究對象
① 年齡60~85歲的人群;② 對認知衰弱有明確診斷標準,即軀體衰弱和認知障礙并存,且排除癡呆及阿爾茲海默癥。
1.1.3 結局指標
① 多因素校正后的死亡率;② 多因素校正后的住院率。
1.1.4 排除標準
① 非中、英文文獻;② 無法獲取全文或重復發表或未發表的文獻;③ 數據信息不完整;④ 原始文獻實驗設計不嚴謹或有誤,如樣本量交代不清或報道有誤的文獻。
1.2 文獻檢索策略
以主題詞和自由詞相結合,計算機檢索VIP、PubMed、CNKI、WanFang Data、CBM、Embase、Cochrane Library和Web of Science等中、英文數據庫,檢索時限均為數據庫建立至2023年5月,英文檢索詞包括:aged/elderly、cognitive decline、cognitive impairment、frail*、cognitive frailty、hospitalization*、mortality*等。中文檢索詞包括:老年人、認知衰弱、認知衰退、認知障礙、衰弱、預衰弱、衰弱綜合征、住院、死亡或不良結局、不良結果等。并采用文獻追溯法,通過人工檢索以提高查全率。
1.3 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
將所有檢索文獻導入NoteExpress進行剔重后,遵循納入及排除標準,由兩名評價者分別單獨進行文獻標題及摘要的閱讀并進行初步篩查,然后進行交叉核對,初步確定納入的合格文獻。若兩人存在異議且經討論后不能達成統一,則交由課題組其他成員參與協商解決。此后,獲取初步納入文獻的全文,由兩名評價者獨立進行全文閱讀,篩查文獻,最終獲得符合納入條件的文獻并提取文獻相關信息。提取內容主要包括:① 納入研究的基本信息,包括第一作者、發表年份、研究國家;② 研究對象的基線特征,包括樣本來源、樣本量、平均年齡;③ 認知衰弱的相關資料,包括認知障礙的評估量表、衰弱的評估量表、認知衰弱發病率;④ 所關注的結局指標與其效應值及95%可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⑤ 調整因素;⑥ 隨訪時間。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由2名研究員分別獨立完成。由于本研究均納入隊列研究,因此均使用紐卡斯爾-渥太華量表(Newcastle Ottawa scale,NOS)[12]進行偏倚風險評價,總分為9分,評分0~3分、4~6分、7~9分依次為低、中、高質量研究。由2名研究員獨立進行文獻篩選、信息提取及偏倚風險評價,若雙方意見不同,則交由第三方進行解決。
1.5 統計分析
采用R 4.2.2軟件進行Meta分析。計數資料采用相對危險度(relative risk,RR)或比值比(odds ratio,OR)或風險比(hazard ratio,HR)為分析統計量,并提供其95%CI。首先采用卡方檢驗進行異質性檢驗,當P≥0.1,I2<50%時,表明研究間異質性較小,使用固定效應模型合并效應量;當P<0.1,I2≥50%時,表明研究間異質性較大,則使用隨機效應模型合并效應量并進行亞組分析[13]。結合Egger’s線性回歸檢驗、漏斗圖及剪補法檢測結局指標(≥10篇文獻)是否存在發表偏倚,用敏感性分析來判定結果的穩定性和可靠性。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文獻檢索結果
初檢共獲得文獻4 768篇,包括PubMed(n=608)、Cochrane Library(n=43)、Embase(n=1 767)、Web of Science(n=1 927)、CNKI(n=43)、WanFang Data(n=72)、VIP(n=233)、CBM(n=75)。經逐層篩選后,最終共納入19項隊列研究,其中以死亡率為結局指標的共11篇;以住院率為結局指標共4篇;同時以死亡率與住院率為結局指標的共4篇。文獻篩選流程和結果見附件圖1。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本研究共納入19項[8-11,14-28]隊列研究,納入研究總樣本量為63 624例,研究對象均為老年人,平均年齡在65.8~82.2歲之間,隨訪時間為30天~14年,認知衰弱患病率為1.6%~37.4%,見表1。
2.3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19項研究在隊列研究的可比性、隨訪時間明確性中描述均較為完整,NOS量表得分均≥7分,為高質量研究。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見附件表1。
2.4 Meta分析結果
2.4.1 認知衰弱與老年人死亡率的關聯
共有15項研究描述認知衰弱與老年人死亡率之間的關系,以不同的衰弱及認知功能狀態、評估工具、研究場所、不同發展程度國家、隨訪時長<5年或5~10年或>10年作為亞組探討異質性來源,亞組分析結果見表2。以認知衰弱為結局的13項[9-11,18,19,21-28]研究結果顯示文獻之間有較高的異質性(I2=78%,P<0.01),因此采用隨機效應模型。認知衰弱的老年人相比于健康的老年人死亡風險顯著增高[OR=2.75,95%CI(2.10,3.59),P<0.01],見附件圖2。
2.4.2 認知衰弱與老年人住院率的關聯
8項研究[8-11, 14-17]描述認知衰弱與老年人住院率之間的關系,以不同的衰弱及認知功能狀態及不同發展程度國家作為亞組探討異質性來源。亞組分析結果見表3。以認知衰弱為結局的7項[8-11, 14-17]研究結果顯示文獻之間有較低的異質性(I2=33%,P=0.17),采用固定效應模型,認知衰弱的老年人相比于健康的老年人發生住院風險更高[OR=1.67,95%CI(1.40,2.00),P<0.01],見附件圖3。
2.5 認知衰弱與老年人死亡率及住院率的敏感性分析
通過逐一剔除單個研究的方法進行敏感性分析。結果顯示合并效應量未出現明顯變化,提示Meta分析結果較穩定,見附件圖4、圖5。
2.6 發表偏倚的檢測
采用Egger’s檢驗對納入死亡率的文獻進行發表偏倚檢驗(t=2.97,P=0.012),說明可能存在發表偏倚,使用剪補法[29]進行矯正,再次行Meta命令計算合并后的效應量[OR=3.06,95%CI(2.44,3.85),P<0.01],與原值[OR=2.75,95%CI(2.10,3.59),P<0.01]差異不大,說明雖有一定的發表偏倚,但原結果是穩定的。由于住院率文獻不足10篇,因此不進行發表偏倚的檢測,見附件圖6、圖7。
3 討論
隨著人口的增加及壽命的延長,全球老齡化人口越來越多,與衰老相關的疾病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關注。認知衰弱作為衰弱的其中一個亞型,于2013年由Kelaiditi等[30]根據國際營養與老年協會及老年病學協會共同提出的共識,將其定義為在排除癡呆的前提下,同時存在身體衰弱及認知障礙的一種老年綜合征。近年來,大量研究開始探討認知衰弱的不良結局,以期提高人們對認知衰弱的重視。
本研究通過Meta分析發現患有認知衰弱的老年人與健康的老年人(本文特指非衰弱且認知功能正常)相比,發生死亡的風險更高,這與Vatanabe等[31]的研究結果相似。但本研究僅納入隊列研究,其時序性因果推斷的可靠性更高且能夠減少回憶及選擇偏倚,另外,近三年有關認知衰弱與死亡的隊列研究不斷增多,有必要再次進行Meta分析以探究認知衰弱與死亡之間的關系。此外,本研究還增加住院率這一結局指標,結果顯示認知衰弱亦會增加老年人住院的風險,但此Meta分析所納入以住院率為結局指標的相關研究數量較少,其結論有待進一步驗證。
研究[32]表明軀體衰弱與認知功能障礙具有相似的病理生理機制,例如線粒體功能障礙和氧化應激反應、炎癥反應以及內分泌失調等。Vermeiren等[33]的研究發現,衰弱作為一種與增齡有關的多種生理系統儲備能力下降的老年綜合征,其主要表現為營養不良、體重減輕、肌肉減少癥、活動水平降低以及難以維持體內平衡這五大因素的復雜相互作用[34],這種多系統不平衡現象主要反映在能量代謝不良及神經肌肉的變化[35],從而可能導致跌倒、殘疾、認知障礙等不良結局的發生。而認知功能可能會影響個體的健康素養,即認知功能障礙的人群難以獲得科學的保健知識及防控指南以維持及促進個體的健康發展,從而更容易出現不良結局[36],Valls-Pedret發現較差的認知能力是較高死亡風險的獨立危險因素[37]。認知衰弱是上述兩者的疊加狀態,兩者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形成惡性循環,對機體帶來更為嚴重的累積效應[38],這與本研究中根據不同衰弱及認知功能狀態進行的亞組分析結果相一致,即與單純衰弱或僅認知障礙組相比,認知衰弱組的老年人發生死亡和住院的風險最高。然而,目前有關認知衰弱增加老年人死亡及住院風險的相關機制尚不明確,因此未來還需有更嚴謹的研究探究認知衰弱與不良結局之間的潛在機制。
雖然本研究結果顯示認知衰弱與老年人死亡率顯著相關,但其結果存在較高的異質性,因此本研究針對不同的衰弱和認知功能狀態、研究場所、評估工具、不同隨訪時間以及不同發展程度國家進行多層亞組分析以進一步探討異質性來源。根據住院及社區兩個不同場所進行亞組分析發現,出現認知衰弱的老年住院患者比存在認知衰弱的社區老年人發生死亡的風險更高,這可能是因為住院的老年患者大多存在共病問題,而這些問題會影響老年人的功能狀態及生活質量,進而增加死亡和住院的風險[39],但目前針對住院老年患者認知衰弱的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相關研究較少,因此未來可開展更多的前瞻性隊列研究,進一步探討住院老年認知衰弱患者的預后情況。此外,隨著隨訪時間的延長,認知衰弱會增加老年人的死亡風險,這可能是與生理上的進展性疾病,如神經退行性疾病或其他慢性疾病有關,另外,長時間的認知衰弱可能導致社會隔離和心理健康問題從而導致老年患者更易受到其他疾病影響[6],進而增加死亡風險。
簡易精神狀態檢查(MMSE)及Fried衰弱表型(FP)是評估認知衰弱最常見的組合,且該組合所定義的認知衰弱的死亡風險相對于認知衰弱與老年人發生死亡風險的總效應值更高。這可能是因為相對于Frail、FI、EFS等衰弱評估工具,FP包含TUGT、握力等客觀指標,對老年人步態、定位轉體能力和肌力的評估更準確,其對身體衰弱的敏感性也更高[40]。此外,根據不同發展程度國家進行亞組分析,結果發現發展中國家存在認知衰弱的老年人與住院率之間的關系無統計學意義,而死亡風險則較發達國家更大。其可能與二者在相關領域的研究水平與醫療保險政策差異有關。認知衰弱的篩查在發達國家已逐步推廣,甚至是探索新興生物標志物以供篩查認知衰弱的老年人[41],而發展中國家相關研究正處于起步階段。這提示我國應當進一步完善老年醫療服務系統,推進社區與住院患者認知衰弱篩查診斷,以盡早預防不良結局的發生從而降低醫療成本。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本研究僅納入中、英文文獻,可能存在語言偏倚;第二,由于納入的隊列研究對認知障礙的診斷存在多種評估量表,因此本研究將認知障礙的評估量表統一歸類為“MMSE/其他量表”并根據不同的衰弱量表進行分類,這導致亞組分析無法判斷不同認知障礙評估量表對研究結局的影響;第三,調整模型中控制不同的變量可能影響認知衰弱對死亡率及住院率的獨立影響大小,但因調整變量過多難以針對不同變量進行亞組分析;第四,由于所納入的研究中大多數未報告HR值,為保證Meta分析的一致性,本研究將效應量統一轉換為OR值,但這損失了部分時間信息。今后可開展更嚴謹的前瞻性隊列研究進一步驗證認知衰弱與老年人死亡及住院的關系。
綜上所述,本研究通過對19項隊列研究進行Meta分析,發現認知衰弱會增加老年人死亡和住院的風險,這提示了醫護人員需要提高對老年人認知衰弱的重視,為社區及醫院針對老年患者開展認知衰弱篩查敲響警鐘,同時為進一步及時開展針對性干預,加強老年人認知衰弱的預防和管理提供重要參考。
聲明 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老年人的健康問題逐漸成為焦點,其中認知衰弱(cognitive frailty)作為健康老齡化[1]及癡呆癥二級預防的新方向[2],已成為國內外老年醫學研究領域的熱點。認知衰弱作為衰弱的一種亞型,是指個體在排除癡呆的前提下,同時存在軀體衰弱與認知功能障礙的臨床狀態[3],其會增加老年人發生跌倒、殘疾、抑郁等不良結局的風險[4-7]。而死亡和住院作為最常見的不良結局指標,是醫護人員尤為關注的重點,既往有研究表明認知衰弱是死亡及住院的獨立危險因素[8],但也有研究認為認知衰弱不會增加死亡[9]或住院[10,11]的風險。目前認知衰弱與老年人發生死亡或住院是否獨立相關在不同研究間尚存在爭議。基于此,本研究將系統檢索已發表文獻,通過Meta分析探究認知衰弱與老年人死亡率和住院率的關系,旨在明確認知衰弱是否會增加老年人死亡和住院的發生風險,為開展早期篩查老年認知衰弱并及時干預提供可靠的依據,以提高老年人的軀體功能和認知水平,最終實現健康老齡化。本研究已在PROSPERO注冊,注冊號為:CRD42023430153。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隊列研究。
1.1.2 研究對象
① 年齡60~85歲的人群;② 對認知衰弱有明確診斷標準,即軀體衰弱和認知障礙并存,且排除癡呆及阿爾茲海默癥。
1.1.3 結局指標
① 多因素校正后的死亡率;② 多因素校正后的住院率。
1.1.4 排除標準
① 非中、英文文獻;② 無法獲取全文或重復發表或未發表的文獻;③ 數據信息不完整;④ 原始文獻實驗設計不嚴謹或有誤,如樣本量交代不清或報道有誤的文獻。
1.2 文獻檢索策略
以主題詞和自由詞相結合,計算機檢索VIP、PubMed、CNKI、WanFang Data、CBM、Embase、Cochrane Library和Web of Science等中、英文數據庫,檢索時限均為數據庫建立至2023年5月,英文檢索詞包括:aged/elderly、cognitive decline、cognitive impairment、frail*、cognitive frailty、hospitalization*、mortality*等。中文檢索詞包括:老年人、認知衰弱、認知衰退、認知障礙、衰弱、預衰弱、衰弱綜合征、住院、死亡或不良結局、不良結果等。并采用文獻追溯法,通過人工檢索以提高查全率。
1.3 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
將所有檢索文獻導入NoteExpress進行剔重后,遵循納入及排除標準,由兩名評價者分別單獨進行文獻標題及摘要的閱讀并進行初步篩查,然后進行交叉核對,初步確定納入的合格文獻。若兩人存在異議且經討論后不能達成統一,則交由課題組其他成員參與協商解決。此后,獲取初步納入文獻的全文,由兩名評價者獨立進行全文閱讀,篩查文獻,最終獲得符合納入條件的文獻并提取文獻相關信息。提取內容主要包括:① 納入研究的基本信息,包括第一作者、發表年份、研究國家;② 研究對象的基線特征,包括樣本來源、樣本量、平均年齡;③ 認知衰弱的相關資料,包括認知障礙的評估量表、衰弱的評估量表、認知衰弱發病率;④ 所關注的結局指標與其效應值及95%可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⑤ 調整因素;⑥ 隨訪時間。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由2名研究員分別獨立完成。由于本研究均納入隊列研究,因此均使用紐卡斯爾-渥太華量表(Newcastle Ottawa scale,NOS)[12]進行偏倚風險評價,總分為9分,評分0~3分、4~6分、7~9分依次為低、中、高質量研究。由2名研究員獨立進行文獻篩選、信息提取及偏倚風險評價,若雙方意見不同,則交由第三方進行解決。
1.5 統計分析
采用R 4.2.2軟件進行Meta分析。計數資料采用相對危險度(relative risk,RR)或比值比(odds ratio,OR)或風險比(hazard ratio,HR)為分析統計量,并提供其95%CI。首先采用卡方檢驗進行異質性檢驗,當P≥0.1,I2<50%時,表明研究間異質性較小,使用固定效應模型合并效應量;當P<0.1,I2≥50%時,表明研究間異質性較大,則使用隨機效應模型合并效應量并進行亞組分析[13]。結合Egger’s線性回歸檢驗、漏斗圖及剪補法檢測結局指標(≥10篇文獻)是否存在發表偏倚,用敏感性分析來判定結果的穩定性和可靠性。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文獻檢索結果
初檢共獲得文獻4 768篇,包括PubMed(n=608)、Cochrane Library(n=43)、Embase(n=1 767)、Web of Science(n=1 927)、CNKI(n=43)、WanFang Data(n=72)、VIP(n=233)、CBM(n=75)。經逐層篩選后,最終共納入19項隊列研究,其中以死亡率為結局指標的共11篇;以住院率為結局指標共4篇;同時以死亡率與住院率為結局指標的共4篇。文獻篩選流程和結果見附件圖1。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本研究共納入19項[8-11,14-28]隊列研究,納入研究總樣本量為63 624例,研究對象均為老年人,平均年齡在65.8~82.2歲之間,隨訪時間為30天~14年,認知衰弱患病率為1.6%~37.4%,見表1。
2.3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19項研究在隊列研究的可比性、隨訪時間明確性中描述均較為完整,NOS量表得分均≥7分,為高質量研究。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見附件表1。
2.4 Meta分析結果
2.4.1 認知衰弱與老年人死亡率的關聯
共有15項研究描述認知衰弱與老年人死亡率之間的關系,以不同的衰弱及認知功能狀態、評估工具、研究場所、不同發展程度國家、隨訪時長<5年或5~10年或>10年作為亞組探討異質性來源,亞組分析結果見表2。以認知衰弱為結局的13項[9-11,18,19,21-28]研究結果顯示文獻之間有較高的異質性(I2=78%,P<0.01),因此采用隨機效應模型。認知衰弱的老年人相比于健康的老年人死亡風險顯著增高[OR=2.75,95%CI(2.10,3.59),P<0.01],見附件圖2。
2.4.2 認知衰弱與老年人住院率的關聯
8項研究[8-11, 14-17]描述認知衰弱與老年人住院率之間的關系,以不同的衰弱及認知功能狀態及不同發展程度國家作為亞組探討異質性來源。亞組分析結果見表3。以認知衰弱為結局的7項[8-11, 14-17]研究結果顯示文獻之間有較低的異質性(I2=33%,P=0.17),采用固定效應模型,認知衰弱的老年人相比于健康的老年人發生住院風險更高[OR=1.67,95%CI(1.40,2.00),P<0.01],見附件圖3。
2.5 認知衰弱與老年人死亡率及住院率的敏感性分析
通過逐一剔除單個研究的方法進行敏感性分析。結果顯示合并效應量未出現明顯變化,提示Meta分析結果較穩定,見附件圖4、圖5。
2.6 發表偏倚的檢測
采用Egger’s檢驗對納入死亡率的文獻進行發表偏倚檢驗(t=2.97,P=0.012),說明可能存在發表偏倚,使用剪補法[29]進行矯正,再次行Meta命令計算合并后的效應量[OR=3.06,95%CI(2.44,3.85),P<0.01],與原值[OR=2.75,95%CI(2.10,3.59),P<0.01]差異不大,說明雖有一定的發表偏倚,但原結果是穩定的。由于住院率文獻不足10篇,因此不進行發表偏倚的檢測,見附件圖6、圖7。
3 討論
隨著人口的增加及壽命的延長,全球老齡化人口越來越多,與衰老相關的疾病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關注。認知衰弱作為衰弱的其中一個亞型,于2013年由Kelaiditi等[30]根據國際營養與老年協會及老年病學協會共同提出的共識,將其定義為在排除癡呆的前提下,同時存在身體衰弱及認知障礙的一種老年綜合征。近年來,大量研究開始探討認知衰弱的不良結局,以期提高人們對認知衰弱的重視。
本研究通過Meta分析發現患有認知衰弱的老年人與健康的老年人(本文特指非衰弱且認知功能正常)相比,發生死亡的風險更高,這與Vatanabe等[31]的研究結果相似。但本研究僅納入隊列研究,其時序性因果推斷的可靠性更高且能夠減少回憶及選擇偏倚,另外,近三年有關認知衰弱與死亡的隊列研究不斷增多,有必要再次進行Meta分析以探究認知衰弱與死亡之間的關系。此外,本研究還增加住院率這一結局指標,結果顯示認知衰弱亦會增加老年人住院的風險,但此Meta分析所納入以住院率為結局指標的相關研究數量較少,其結論有待進一步驗證。
研究[32]表明軀體衰弱與認知功能障礙具有相似的病理生理機制,例如線粒體功能障礙和氧化應激反應、炎癥反應以及內分泌失調等。Vermeiren等[33]的研究發現,衰弱作為一種與增齡有關的多種生理系統儲備能力下降的老年綜合征,其主要表現為營養不良、體重減輕、肌肉減少癥、活動水平降低以及難以維持體內平衡這五大因素的復雜相互作用[34],這種多系統不平衡現象主要反映在能量代謝不良及神經肌肉的變化[35],從而可能導致跌倒、殘疾、認知障礙等不良結局的發生。而認知功能可能會影響個體的健康素養,即認知功能障礙的人群難以獲得科學的保健知識及防控指南以維持及促進個體的健康發展,從而更容易出現不良結局[36],Valls-Pedret發現較差的認知能力是較高死亡風險的獨立危險因素[37]。認知衰弱是上述兩者的疊加狀態,兩者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形成惡性循環,對機體帶來更為嚴重的累積效應[38],這與本研究中根據不同衰弱及認知功能狀態進行的亞組分析結果相一致,即與單純衰弱或僅認知障礙組相比,認知衰弱組的老年人發生死亡和住院的風險最高。然而,目前有關認知衰弱增加老年人死亡及住院風險的相關機制尚不明確,因此未來還需有更嚴謹的研究探究認知衰弱與不良結局之間的潛在機制。
雖然本研究結果顯示認知衰弱與老年人死亡率顯著相關,但其結果存在較高的異質性,因此本研究針對不同的衰弱和認知功能狀態、研究場所、評估工具、不同隨訪時間以及不同發展程度國家進行多層亞組分析以進一步探討異質性來源。根據住院及社區兩個不同場所進行亞組分析發現,出現認知衰弱的老年住院患者比存在認知衰弱的社區老年人發生死亡的風險更高,這可能是因為住院的老年患者大多存在共病問題,而這些問題會影響老年人的功能狀態及生活質量,進而增加死亡和住院的風險[39],但目前針對住院老年患者認知衰弱的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相關研究較少,因此未來可開展更多的前瞻性隊列研究,進一步探討住院老年認知衰弱患者的預后情況。此外,隨著隨訪時間的延長,認知衰弱會增加老年人的死亡風險,這可能是與生理上的進展性疾病,如神經退行性疾病或其他慢性疾病有關,另外,長時間的認知衰弱可能導致社會隔離和心理健康問題從而導致老年患者更易受到其他疾病影響[6],進而增加死亡風險。
簡易精神狀態檢查(MMSE)及Fried衰弱表型(FP)是評估認知衰弱最常見的組合,且該組合所定義的認知衰弱的死亡風險相對于認知衰弱與老年人發生死亡風險的總效應值更高。這可能是因為相對于Frail、FI、EFS等衰弱評估工具,FP包含TUGT、握力等客觀指標,對老年人步態、定位轉體能力和肌力的評估更準確,其對身體衰弱的敏感性也更高[40]。此外,根據不同發展程度國家進行亞組分析,結果發現發展中國家存在認知衰弱的老年人與住院率之間的關系無統計學意義,而死亡風險則較發達國家更大。其可能與二者在相關領域的研究水平與醫療保險政策差異有關。認知衰弱的篩查在發達國家已逐步推廣,甚至是探索新興生物標志物以供篩查認知衰弱的老年人[41],而發展中國家相關研究正處于起步階段。這提示我國應當進一步完善老年醫療服務系統,推進社區與住院患者認知衰弱篩查診斷,以盡早預防不良結局的發生從而降低醫療成本。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本研究僅納入中、英文文獻,可能存在語言偏倚;第二,由于納入的隊列研究對認知障礙的診斷存在多種評估量表,因此本研究將認知障礙的評估量表統一歸類為“MMSE/其他量表”并根據不同的衰弱量表進行分類,這導致亞組分析無法判斷不同認知障礙評估量表對研究結局的影響;第三,調整模型中控制不同的變量可能影響認知衰弱對死亡率及住院率的獨立影響大小,但因調整變量過多難以針對不同變量進行亞組分析;第四,由于所納入的研究中大多數未報告HR值,為保證Meta分析的一致性,本研究將效應量統一轉換為OR值,但這損失了部分時間信息。今后可開展更嚴謹的前瞻性隊列研究進一步驗證認知衰弱與老年人死亡及住院的關系。
綜上所述,本研究通過對19項隊列研究進行Meta分析,發現認知衰弱會增加老年人死亡和住院的風險,這提示了醫護人員需要提高對老年人認知衰弱的重視,為社區及醫院針對老年患者開展認知衰弱篩查敲響警鐘,同時為進一步及時開展針對性干預,加強老年人認知衰弱的預防和管理提供重要參考。
聲明 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